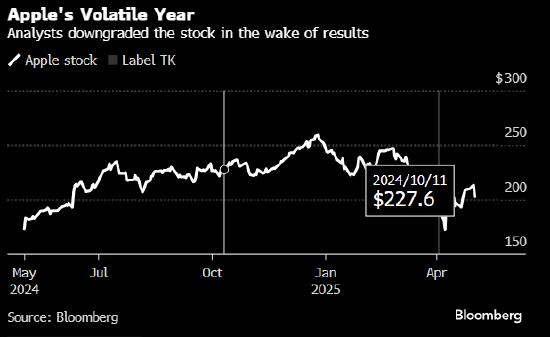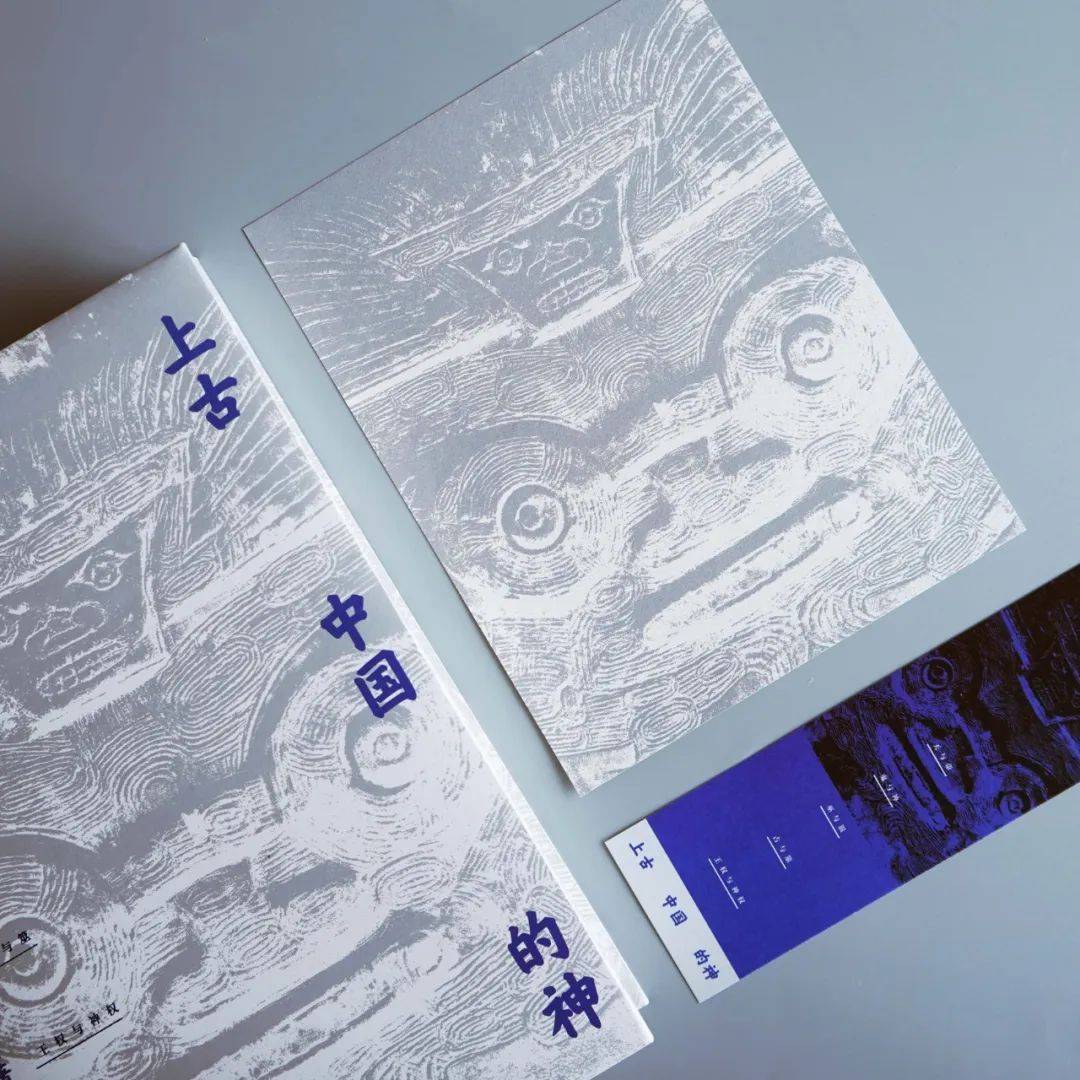
现代人大抵都是这样:当人生大事难以抉择时,就想着要不要去算个命、求个签、转个运。其实,这种本能似的对神的依赖,从上古时代开始就刻在我们的DNA里了。今天我们推荐的《上古中国的神》一书网络配资炒股网站,由先秦史研究大家晁福林先生写作。在本书中,晁先生分别以“天与帝”“鬼与神”“巫与诅”“占与筮”“王权与神权”为主题,对先秦时期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你可以把这本书理解为一幅中国古代的精神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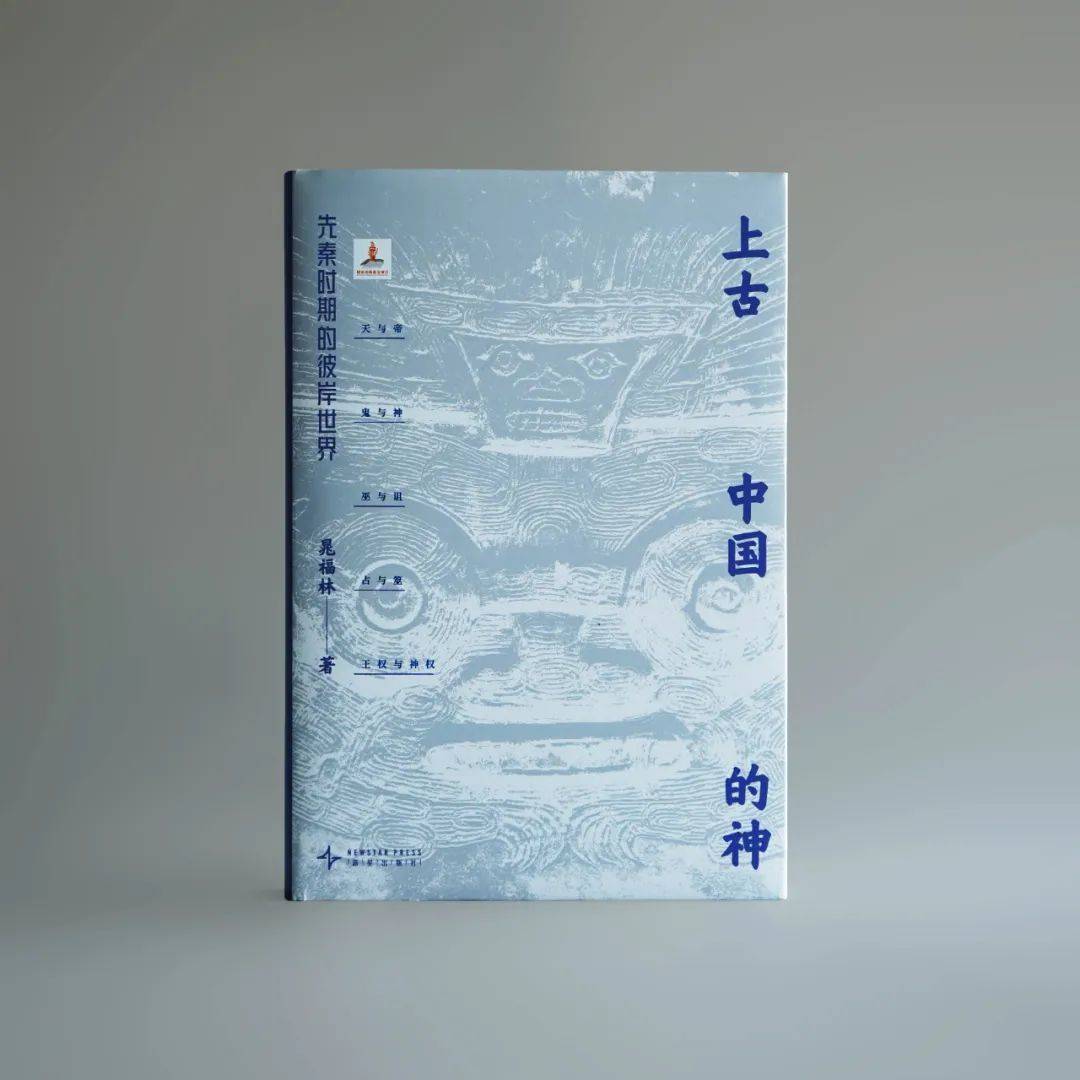
作者: 晁福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先秦时期(主要是商周,上溯到远古),人们想象中的“彼岸世界”及其核心的组成部分——神灵体系。它讲述了古人是如何从“人与动物杂糅”的原始思维,一步步构想出丰富多彩的神灵与死后世界的。它探讨了,是中国人“信仰”与“生命观”的源头情绪共鸣角度: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有些共鸣是刻在 DNA 里的——理解了过去也就能够更好的面对未来。比如说:对死的恐惧,催生出的往往是对生的热爱;对远方的幻想,映照出的往往是对现实的反思。
作者晁福林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晁先生说,先秦时期,天、帝、鬼、神等观念深入人心,为应对之,巫、诅、占、筮等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乃至社会最高权力起初也是以“神主”的面貌出现的。这些思想和观念是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对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内容丰富,今天,我们先带读者看看晁老师对《山海经》中“天”这个观念的观察,这个如今被我们赋予诸多意义的意向,在当时,仅作为神居处所而存在,尚未形成后世抽象化的天命或义理概念。
以下内容,摘自《上古中国的神》,作者:晁福林。由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
《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天”观念
(“天”观念的滥觞与发展)
《山海经》虽编定于西汉末年,但其写成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书诸篇皆在诸子蜂起的时候,由好奇嗜古之士“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汇集上古传说而成。此书内容驳杂奇特,专家多关注其历史地理方面的记载,而较少关注其中所载的上古先民的思想观念问题,特别是关于其中“天”的观念则更鲜有专门研究。今述其要以窥见上古时代“天”观念的若干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山海经》是追述传说时代“天”观念的最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在《山海经》里,“天”只用在名词之前,表示作为处所的“天空”。在天上生活着“帝”及其他各种神人。在《山海经》里,“天”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具有抽象意义的概念。冯友兰先生早曾提出的“天”之五义,在《山海经》时代尚未出现。今由此线索依次讨论。
若谓在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观念,“天命”观念当名列其中。“天命”观的出现和形成是中国上古时代思想史上的大事。这种影响很大并且十分久远的社会观念,其出现和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时段才臻于完成的,它肇端于对于“天”的印象及认识。我们对此可以做一概述,以期了解“天命”观念形成的历史路径。
关于上古先民对于“天”的认识经历,我们可以先从理论上做如下的概述。在漫长而遥远的远古时代,先民印象中的“天”应当是无限深远的天空,它启迪了先民的好奇之心,先民对于天空的兴趣增长,使得人们对于天空进行最直接的观察与思索,渐渐充满了虔敬、疑惑与联想。在这之后,远古先民对于天的认识逐渐丰富,在先民的印象里,“天”不再是没有实体存在的天之“空”,而是逐渐把地上的美景、美居、美之山水、美之树木花草移到天上,使空空如也之“天”成为美好而诗意的神仙之居。这个时期的“天”,是作为处所之意念存在于人们印象之中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在上古先民的意识中逐渐将“天”抽象化,由形象的自然之天,渐至成为抽象的神灵之天,天之神性渐渐增加,而天之作为处所的物性则相应地减少。这个阶段的最后的过程就是“天”之权威性增强,在神灵世界里其地位上升,天命观念形成。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阶段,对于天之决定性的思考,逐渐衍生出天之理性,使天减少了人格,而侧重于义理,有了终极的规律与趋势的意蕴。简言之,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天命之天——义理之天,应当就是我国先秦时期这个长时段里面天命观念起源、产生、演化的主要阶段。这每一个阶段,除了新萌生的观念之外,传统的观念依然保存,可以说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这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是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完成的。当然,上述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约略推测,实际情况应当是极其复杂而曲折的。
关于“天”之意蕴,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冯友兰先生就精辟地指出:
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 · 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
将古代笼统的“天”的观念分为“五义”来认识,实为一个重要发现。天之“五义”说,是一个相当全面而精辟的论析,“天”之意蕴大体若是,冯先生的这个分析至今也未过时。
我们于此应当指出的是,冯先生所言“天”之五义,已经强调了是“文字”(而非传说)的“天”。现在我们来探讨“天”观念的问题,可以在冯先生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进而明确指出,“五义”之“天”并非同时形成的观念,而是经历漫长时段方逐渐形成和完备的,并且传说与文字记载的“天”,有着相当的区别,似不可以用“五义”来衡量传说时代的“天”。
上古传说时代,先民对于“天”的观念只有“自然之天”的一些萌芽。直到殷商时期,我们从甲骨卜辞中才看到“天”有逐步神化的迹象。商代被神化的“天”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卜辞中凡言“帝”令风雨雷雹者,皆可换称为“天”令风雨雷雹;凡言“帝”降旱、降祸者,皆可换称“天”降旱、降祸;凡言“帝”若、不若者,皆可换称“天”若、不若;凡言“帝”受(授)又(佑)者,皆可换言“天”授佑。这时期的上古先民的“天”“帝”观念中的神性只是开始渐渐增强,那个主宰天下命运的“上帝”还只是一个“隐蔽的上帝”。
若谓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可以主宰一切的“上帝”,周代所说的“天命”与之约略相当。2 这个“上帝”直到周代才戴着“天命”的面具从隐蔽的后台“闪亮”登场。到了这个时候,“天”观念的早期要义的两个主要方面(即自然之天和“天命”之天)初步具备。上古时期的“天”“帝”融一的情况,到了周代虽然发生了变化(“天”主要指自然之天,而“帝”则主要指天神),但“天”和“帝”还时常通假,带着两者曾长时间融而为一的痕迹。顾颉刚先生曾精辟分析上古时代的“天”“帝”二字音近字通的情况,今具引如下:
“帝”与“天”为同纽字,故二字常通用。《诗 · 商颂· 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生商者“天”也而即“帝”也。《周颂· 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 文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所配者“天”也而即“帝”也。……又说商之孙子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发此命者“帝”也而即“天”也。凡此种种,皆足证“帝”与“天”为互文。
“帝”字古音属端纽,“天”字属透纽,皆舌头音,顾先生说两者声纽同,是正确的。就声(韵)部来说,“帝”的古音属锡部,“天”属真部,两者为阴入对转。4 这两个字古音接近,有通假的条件。我们说的这两个字的古音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音,可以推测,两者融而为一的时候,发音相同,随着意义的分化,其声、韵才发生了分离。“帝”与“天”的通假,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古音,而在于两者初始意义的同一。因为两者起初为一,所以古音必然相同。后来,意义发生分化,其声纽和韵部也随之而略有所变。“天”与“帝”的通假,是主要因由意同而通假的较典型的例子。具体分析两者相通假的用例,会发现“天”与“帝”相通假的时候,用的是神化了的“天”之意,而不是与自然之天相通假。反过来说,“帝”只与神化了的“天”相通假,而不与自然之“天”相通假。
从上古先民质朴的“天”观念发展到周代的“天命”观念,经历了漫长的时段。“天命”,简言之,就是天对于社会与个人命运的安排。天命的安排,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撼动的最高权威。天命观念的起源与演变,特别是在远古时代,先民智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进步得尤其缓慢。传说时代天命观的发展进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其进步速度的差距不啻天壤之别。从“天”到“天命”,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却跨越了数千年之久才臻至完成。此正如黑格尔讲“概念”的普遍性时所说:“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我们必须说,费了许多千年的时间,思想才进入人的意识。” “天”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世代相传的上古先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此一概念传承的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的诸概念中可谓独占鳌头。按照黑格尔“许多千年”的说法,我国上古先民对于“天”的印象和认识,再逐渐形成社会的共识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而成为一种社会思想,这一过程绵延了从传说时代到商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段乃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新星出版社
卫诗雅 变与不变 始终赤诚
史依弘 与京剧的百年对谈
王芊懿&王柳懿 “她”漾精彩
李娜 刚柔并济 逐冠人生
王羽佳:探索不止 恒动不息
汪顺:年龄只是数字 实力说明一切
新 刊
「 2025年7月31日 袁莎 」网络配资炒股网站
信康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